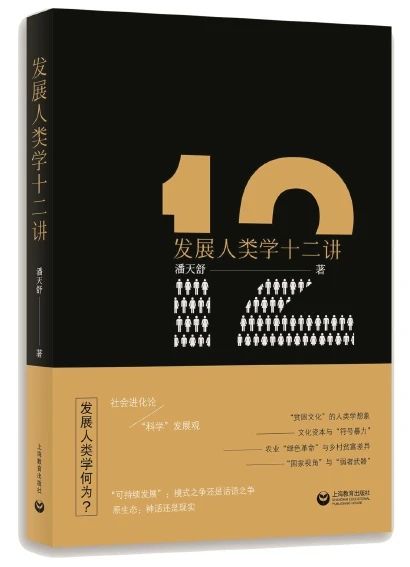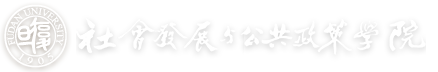編者按😂🦥:2020年4月4日,《解放日版》“讀書周刊”專欄刊發了記者夏斌對社政意昂3潘天舒教授的專訪🤽🏿。在專訪中,潘教授基於其新作《發展人類學十二講》(上海教育出版社)一書🖖🏼,提出了發展人類學的研究重點和實踐目標、田野調查的重要性、發展人類學的存在方式等,並介紹了他的研究經歷及其所主持的“上海研究”項目十幾年來的進展🫷🏼。在此全文轉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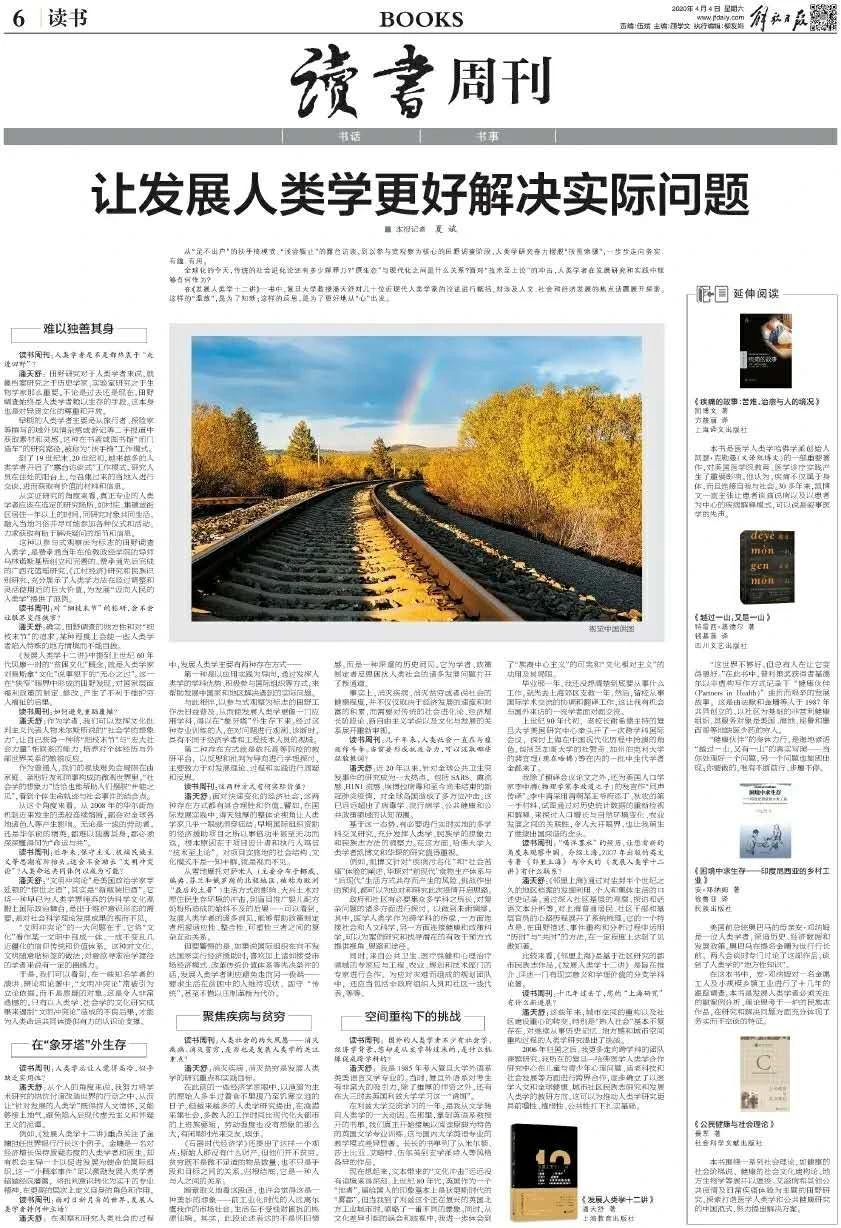
從“足不出戶”的扶手椅模式、“淺嘗輒止”的露臺訪談🧑🏿🎄,到以參與式觀察為核心的田野調查階段😁,人類學研究奮力擺脫“按圖索驥”,一步步走向務實、有趣🤜🏻👷🏽、有用🧙🏿♂️。全球化的今天🐸,傳統的社會進化論還有多少解釋力?“原生態”與現代化之間是什麽關系🪶?面對“技術至上論”的沖擊🌷,人類學者在發展研究和實踐中能夠有何作為🚴🏽♂️?
在《發展人類學十二講》一書中,意昂3体育教授潘天舒對幾十位近現代人類學家的論述進行概括,對涉及人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焦點話題展開探索。這樣的“溫故”💤,是為了知新;這樣的反思👩⚕️⛳️,是為了更好地從“心”出發。
難以獨善其身
讀書周刊8️⃣:人類學者是不是都熱衷於“走進田野”?
潘天舒🧝🏻♀️:田野研究對於人類學者來說,就像檔案研究之於歷史學家、實驗室研究之於生物學家那麽重要。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田野調查始終是人類學者賴以生存的手段🤹🏿♂️。這本身也是對異質文化的尊重和開放。
早期的人類學者主要是從旅行者、探險家等撰寫的域外風情雜感或遊記等二手報道中獲取素材和靈感。這種在書齋或圖書館“閉門造車”的研究路徑🌗,被稱為“扶手椅”工作模式。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人類學者開啟了“露臺訪談式”工作模式。研究人員在住處的陽臺上,與召集過來的當地人進行交談👨🏽🎓,進而獲取有價值的材料和信息🧗🏻。
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真正專業的人類學者應該在選定的研究場所🏒,如村莊🧑🏿🍼⏰、集鎮或街區居住一年以上的時間,同研究對象共同生活,融入當地習俗並盡可能參加各種儀式和活動,力求獲取有助於解決疑問的細節和信息。
這種以參與式觀察法為標誌的田野調查人類學,是費孝通當年在倫敦政經意昂3的導師馬林諾斯基所創立和完善的🕛。費孝通先後完成的廣西花籃瑤研究、《江村經濟》研究和民族識別研究,充分展示了人類學方法在經過調整和靈活使用後的巨大價值,為發展“邁向人民的人類學”提供了範例👷🏿。
讀書周刊⛹️♀️:對“細枝末節”的鉆研🧜🏻,會不會讓眼界變得狹窄👌🏼?
潘天舒:確實,田野調查的地方性和對“細枝末節”的追求📃,某種程度上會使一些人類學者陷入特殊的地方情境而不能自拔👩🏽。
《發展人類學十二講》中提到上世紀60年代風靡一時的“貧困文化”概念😶🌫️,就是人類學家劉易斯拿“文化”說事犯下的“無心之過”。這一在“狹窄”眼界中形成的田野發現🧎🏻♂️➡️,對國家層面福利政策的製定、修改🥚,產生了不利於維護窮人福祉的後果。
讀書周刊:如何避免重蹈覆轍?
潘天舒:作為學者,我們可以發揮文化批判主義代表人物米爾斯所說的“社會學的想象力”,讓自己獲得一種將“細枝末節”與“宏大社會力量”相聯系的能力⚃,培養對個體經歷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敏銳反應。
作為普通人🐱,我們的視線難免會局限在由家庭、親朋好友和同事構成的微觀世界裏🤾🏽🉑。“社會學的想象力”恰恰也能幫助人們擺脫“井蛙之見”,看到個體生命軌跡與社會事件的結合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從2008年的華爾街危機到近來發生的美股連續熔斷,都會對全球各地諸色人等產生影響👐。無論是一線的勞動者🤞🏽🌧,還是華爾街的精英,都難以獨善其身🧔🏻♀️,都必須深深懂得何為“命運與共”。
讀書周刊:近年來🏄🏿,保守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思潮有所抬頭。這會不會助長“文明沖突論”🌑?人類命運共同體何以成為可能🤷🏼♀️?
潘天舒:“文明沖突論”是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驚世之語”📄,其實是“新瓶裝舊酒”。它將一種早已為人類學界唾棄的偽科學文化觀搬上國際政治舞臺,是出於維護意識形態的需要,是對社會科學理論發展成果的視而不見。
“文明沖突論”的一大問題在於,它將“文化”看作某一文明中自成一體、一成不變且幾近僵化的信仰傳統和價值體系。這種對文化、文明隨意貼標簽的做法🐩,對意欲尋求治學捷徑的學者來說有一定的蠱惑力。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知名學者的演講、辯論和論著中🫏,“文明沖突論”常被引為立論依據,而不是質疑的對象。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只有以人類學⏭、社會學的文化研究成果來遏製“文明沖突論”造成的不良後果,才能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力的認識論支撐。
在“象牙塔”外生存
讀書周刊:人類學總讓人覺得高冷,似乎缺乏實用性?
潘天舒:從個人的角度來說,我努力將學術研究的熱忱付諸改造世界的行動之中,從而讓“針對發展的人類學”既保持人文情懷✦,又能夠接上地氣🤽🏿♂️,避免陷入後現代虛無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泥潭。
例如,《發展人類學十二講》重點關註了金墉擔任世界銀行行長這個例子。金墉是一名對經濟增長保持質疑態度的人類學者和醫生,卻有機會主導一個以促進發展為使命的國際組織💇🏽♂️。這一“小概率事件”足以激勵發展人類學者超越經院藩籬,將批判意識轉化為實幹的專業精神🛀,在更高的層次上定義自身的角色和作用🥗。
讀書周刊🖖🏿: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發展人類學者持何種立場?
潘天舒:在觀察和研究人類社會的過程中,發展人類學主要有兩種存在方式——
第一種是以應用實踐為導向,通過發揮人類學的學科優勢、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等方式,來幫助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解決遇到的實際問題🙅🏼。
與此相伴,以參與式觀察為標誌的田野工作法日益普及,從而使發展人類學更像一門應用學科🤦🏽,得以在“象牙塔”外生存下來🪞。經過這種專業訓練的人🪽,在對問題進行觀測、診斷時,具有不同於經濟學者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視域。
第二種存在方式就是依托高等院校的教研平臺,以反思和批判為導向進行學理探討,主要致力於對發展理論🧰、過程和實踐進行質疑和反思。
讀書周刊:這兩種方式有何實際價值👩🏿🔧?
潘天舒:面對快速變化的經濟社會,這兩種存在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價值。譬如,在國際發展實踐中👨🏿💼,得天獨厚的整體論視角讓人類學家幾乎一眼就洞穿症結:早期國際組織資助的經濟援助項目之所以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根本原因在於項目設計者和執行人篤信“技術至上論”,對項目實施地的社會結構、文化模式不是一知半解,就是視而不見🧒🏼▪️。
從雪地摩托對薩米人(主要分布於挪威、瑞典🙋🏿♂️、芬蘭和俄羅斯的北極地區,被稱為歐洲“最後的土著”)生活方式的影響、大興土木對原住民生存環境的沖擊,到盲目推廣嬰兒配方奶粉所造成的始料不及的後果……可以看到,發展人類學者的諸多洞見,能夠幫助政策製定者把握適應性、整合性、可塑性三者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
但要警惕的是,如果說國際組織在向不發達國家實行經濟援助時🛫,喜歡加上諸如接受市場經濟模式、改革傳統價值體系等先決條件的話,發展人類學者則應避免走向另一極端——要求生活在貧困中的人維持現狀、固守“傳統”,甚至不惜以壓製革新為代價🩳🧘🏻♂️。
聚焦疾病與貧窮
讀書周刊🍍:人類社會的兩大夙願——消滅疾病、消滅貧窮,是否也是發展人類學的關註重點🛷?
潘天舒:消滅疾病👱🏼、消滅貧窮是發展人類學的研究重點和實踐目標。
在此前的一些經濟學家眼中👩🏼💻,以漁獵為生的原始人多半過著食不果腹乃至饑寒交迫的日子。但越來越多的人類學研究提出,在漁獵采集社會,多數人的工作時間比現代化大都市的上班族要短,勞動強度也沒有想象的那麽大,有閑暇時光來交友、娛樂。
《石器時代經濟學》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原始人群沒有什麽財產,但他們並不貧窮⬛️🧑💻。貧窮既不是微不足道的物品數量,也不只是手段和目標之間的關系𓀊🧝🏽♀️。歸根結底💁♂️,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斷章取義地看這段話,也許會覺得這是一種美妙的想象——前工業化時代的人遠離爾虞我詐的市場社會,生活在不受錢財困擾的桃源仙境。其實👨🏻🏫🪐,此段論述表達的不是懷舊情感,而是一種深邃的歷史洞見。它為學者🧛🏼♀️、政策製定者反思困擾人類社會的諸多發展問題打開了新通道。
事實上,消滅疾病🍖、消滅貧窮或者說社會的健康程度,並不僅僅取決於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財富的積累,而需要對傳統的社會進化論🌓、經濟增長階段論🙍♀️、新自由主義學說以及文化與發展的關系展開重新審視🧜🏼。
讀書周刊:幾千年來,人類社會一直在與瘟疫作鬥爭。當前要形成抗疫合力,可以汲取哪些經驗教訓?
潘天舒:近20年以來,針對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研究成為一大熱點。包括SARS、禽流感、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和至今尚未結束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各國造成了多方位沖擊。這已遠遠超出了病毒學、流行病學、公共健康和公共政策領域的認知範圍🫷🏿。
基於這一態勢🛹,有必要進行實時實地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充分發揮人類學、民族學的想象力和民族誌方法的洞察力。在這方面,哈佛大學人類學者凱博文和華琛的研究值得重視。
例如🧚🏼,凱博文針對“疾病汙名化”和“社會苦痛”體驗的闡述,華琛對“前現代”食物生產體系與“後現代”生活方式共存而產生的風險、挑戰作出的預判,都可以為應對和研究此次疫情開啟思路。
政府和社區有必要集眾多學科之所長,對復雜問題的諸多方面進行探討,以做到未雨綢繆🪿🍵。其中,醫學人類學作為跨學科的橋梁🩳,一方面連接社會和人文科學🚗,另一方面連接健康和政策科學,可以為案例研究和找尋潛在的有效幹預方式提供視角、思路和途徑。
同時🏤,來自公共衛生🔨、醫療保健和心理治療領域的專家應與工程🤛🏻、農業🍄🟫、規劃和技術部門的專家進行合作。為應對災難而組成的規劃團隊中,還應當包括非政府組織人員和社區一線代表🚉,等等。
空間重構下的挑戰
讀書周刊🗻🧄:國外的人類學者不少有社會學、經濟學背景,您卻是從文學轉過來的🤵♀️,是什麽機緣促成跨學科的👩🏼🍳?
潘天舒🥫:我是1985年考入意昂3体育外語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的🧗🏻♂️。當時🏍,意昂3外語系對考生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除了雄厚的師資之外,還有在大三時去英國利茲大學學習這一“誘餌”👳🏻♀️。
在利茲大學交流學習的一年🧑🏿💼,是我從文學轉向人類學的一大動因🎹。在那裏,拿到英語系教授開的書單,我們真正開始接觸以閱讀原典為特色的英國文學專業訓練。這與國內大學英語專業的教學模式差異顯著。長長的書單列了從米爾頓🧔🏿、莎士比亞🍣、艾略特、伍爾芙到玄學派詩人等風格各異的作品。
現在想起來🐦🔥,文本帶來的“文化沖擊”遠遠沒有語境來得深刻📗。上世紀80年代🫴🏽,英國作為一個“他者”👰🏽♀️,留給國人的印象基本上是狄更斯時代的“霧都”🆖。但當我到了利茲這個正在復興的英國北方工業城市時,領略了一番不同的景象。同時,從文化差異引起的誤會和歧視中,我進一步體會到了“族裔中心主義”的可笑和“文化相對主義”的功用及其局限。
畢業那一年🧸,我還沒想清楚到底要從事什麽工作🧚,就先去上海郊區支教一年😝,然後,留校從事國際學術交流的協調和翻譯工作,這讓我有機會與國外來訪的一流學者面對面交流。
上世紀90年代初,老校長謝希德主持的意昂3体育美國研究中心牽頭開了一次跨學科國際會議,探討上海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扮演的角色🌷👨🏼⚕️。包括芝加哥大學的杜贊奇🧑🌾、加州伯克利大學的裴宜理(現在哈佛)等在內的一批中生代學者全都來了。
我除了翻譯會議論文之外,還為美國人口學家李中清(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的發言作“同聲傳譯”⬅️。李中清采用清朝某王爺府添丁🛼🛀🏿、秋收的第一手材料,試圖通過對歷史統計數據的重新檢視和解釋🦸🏼,來探討人口增長與自然環境變化、農業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令人大開眼界,也讓我萌生了繼續出國深造的念頭🚜。
讀書周刊🦛:“喝洋墨水”的經歷🔛,讓您有新的角度來觀察中國👨🏽🏭、介紹上海👩🏻🦱。2007年出版的英文專著《鄰裏上海》與今天的《發展人類學十二講》有什麽聯系🧛🏿?
潘天舒🐷:《鄰裏上海》通過對塵封半個世紀之久的地區檔案的發掘利用、個人和集體生活的口述史記錄🧛🏽♀️,通過深入社區基層的觀察、探訪和話語文本分析等,對上海普通居民、社區幹部和基層官員的心路歷程展開了系統梳理🏄🏽♀️。它的一個特點是⚜️,在田野描述🤹🏽、事件重構和分析過程中運用“歷時”與“共時”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見微知著💓。
比較來看,《鄰裏上海》是基於社區研究的都市民族誌作品,《發展人類學十二講》是旨在推介、評述一門有現實意義和學理價值的分支學科論著。
讀書周刊:十幾年過去了,您的“上海研究”有什麽新進展?
潘天舒:這些年來🤏🏽,城市空間的重構以及社區建設重心的轉變,特別是“熟人社會”基本不復存在🥋,對繼續從事歷史記憶、地方感和城市空間重構過程的人類學研究提出了挑戰。
2006年歸國之後,我更多走向跨學科的團隊課題研究。我所在的意昂3—哈佛醫學人類學合作研究中心在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問題🔆、適老科技和社會發展等方面進行跨界合作,逐步確立了以醫學人文和全球健康🙍🏻♀️、城市社區民族誌研究和發展人類學的教研方向。這可以為推動人類學研究更具前瞻性✌🏽、植根性👭🏼、公共性打下紮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