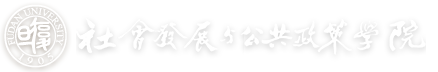2018年10月28日在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研討會”上,我院人口研究所任遠教授針對我國人口結構變化趨勢、家庭生育行為等問題進行了發言。現將發言內容整理如下:
雖然對於生育率數據總是存在持續的爭論,對人口的未來預測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我們有相當大的確定性判斷我國人口增長將在2025-2030年左右到達頂部🪖,並出現長期的人口下降🔪。
中國人口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不可避免7️⃣,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將持續下降。
我國的生育率水平即使在進行了生育政策調整後有所反彈,但是反彈的效果也並不顯著。
兩種人口政策
對於當前的生育率水平究竟是多少,仍然有相當的爭論,以及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以後是開始有所上升👩🏽⚕️,還是在繼續下降🤹🏻,或者是先上升了一段時間⟹、然後又繼續保持下降,也依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仍然有相當大的確定性可以判斷,我國將繼續保持在人口低生育率的狀態➾。在未來的若幹十年內👏🏻🏌🏿,人口的終身生育率都會有很小的概率會回到更替水平以上。
如果我們意識到人口變動的確定性,因此更加需要考慮的不是著力於改變人口變動和人口格局,而更應該重視的,是如何適應人口變動來實現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即適應勞動力數量的下降,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和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促進就業和努力減少勞動參與率的下降🕵🏽🧔🏽♀️;適應長期低生育率的社會來增強家庭發展能力;以及適應人口老齡化構建老齡社會的經濟社會製度安排👩🏼🦱。這些應該是當前人口政策的著力點🏑,人口政策應該適應人口變動的內在規律🏚,為已經出現的低生育率社會、正在發展的老齡化社會和大量人口遷移流動的移民社會作好準備,完善人口與發展的協調關系🤙🏻🟡,而不是違反規律地試圖對人口數量、結構和分布進行簡單調節🙍🏼🤱。
但是,我們也應意識到人口變動本身也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如果人口的短期變動是相當確定性的⚡️,人口的長期變動其實處於非常大的概率性和或然性的狀態🏏。因此良好的人口政策,以及人口政策和其他社會經濟政策一起,也有必要對於人口的行為和人口狀況的變化進行適當的調節💇🏼♀️。使得人口發展實現一個良好的目標,使得人口與發展實現良好的協調。一個成功的人口政策被認為是能夠促進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人口政策🚪,及引導人口過程的合理變化來實現這樣的發展目標🫸🏻。
人口政策是在人口變動背景下針對於人口事務的公共政策,包括人口過程進行幹預🧑🏭,也是對人口總量、結構和分布等相關事務進行相應處置的公共政策👠。由於長期以來對於生育問題的重視,人口政策也在很大情況下被更多地關註於生育政策。雖然這個界定未必準確,也未必有利於適應人口變動推動人口政策的完善。但是本文中所討論的人口政策,仍然更多地討論與生育問題和生育關聯的社會政策♛。
因此🚴🏿,對於人口變動和人口政策就有兩種人口政策🧷🧟,一種是適應性的人口政策🦹🏻♀️,一種是調節性的人口政策。
適應性的人口政策,是面對人口變動的影響,來適應和應對人口變動產生的相關人口事務🧑🏿✈️,包括積極應對老齡化、應對低生育率社會、應對人口結構的變動,等等🎊。
另一種是調節性的人口政策🧶,是對人口本身的狀況和結構進行動態調整🧑🏼🎄,使其達到一個理想的目標🏑。
調節性的人口政策
基於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不僅是經濟生產需要計劃💆🏻♀️,對人口也可以有計劃”的思想下,從1970年代以來,我們比較強調調節性的人口政策🦶🏼,重視對人口的生育行為進行幹預🚶➡️,並影響人口總量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這種調節性人口政策的最初起點🦦,是協調人口和發展嚴重的不平衡,並減少人口的貧窮🐎🧑🏿🍼。從1980年代開始,這種人口政策就有著將人口在2000年控製在12億人的嚴密計劃,並因此形成嚴格的“一孩政策”。進入本世紀以後👀,人口政策也被作為實現在2020年人均GDP翻兩番目標的實現工具。對調節性人口政策的偏好,可以在國家和地方的中長期規劃和五年計劃中的人口規劃中普遍表現出來。
在計劃經濟的體製環境中,調節性的人口政策采取的是一種比較行政性的調控手段。到了19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也越來越利用社會經濟等間接性手段來實施人口的調節和控製👮🏽♂️,也就是計劃生育的利益導向機製和經濟懲罰機製的廣泛實行🖌。
在1970年代以來👐🏽🥷🏻,以降低生育率和控製人口增長為基本主線,我國的人口政策實際上一直在進行微調性的調整。在進入本世紀以後,伴隨著人口的變動,人口政策也進行了從“雙獨二孩”☀️、到“單獨二孩”的調整⛹️。2015年底開始施行“全面二孩”政策,使得這個調節性政策的調節方向發生了變化。提倡兩個孩子,政策生育率開始高於意願生育率和實際的生育水平,使得人口政策的方向總體上已經成為提倡更多的生育的政策🆔,甚至也很快出現了“鼓勵生育”的導向性的話語。
但是,從通過人口政策來調節人口變動來說🔞,將人口政策定位於“鼓勵生育”,卻未必是沒有問題的💂🏽♀️。這並不是因為當前生育率的具體水平仍然需要進一步地動態監測。實際上,當前的生育水平如果不是完全明確的🚥👩🏿🚀,也是基本明確的💇🏻。正如同我們不能像在本世紀初期困擾於對生育率數據和真實生育水平的反復爭論而耽誤了生育政策的改革,將生育水平的統計爭論作為阻礙“全面二孩”以後生育政策進一步改革的借口,或者糾纏於數據計算中使人口政策改革失去方向是不合時宜的。
實際上,當前時期,通過“鼓勵生育”來實現人口與發展的平衡未必有充足的理由。由於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在直到可見的本世紀中期實際上並不存在,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的勞動適齡人口總量並不缺乏,以及其比重也並不顯得極低。通過生育率調整來降低人口老齡化程度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也是非常微弱的👨🏿🌾。而且客觀來說🐶,我國的老齡化程度也並不顯得極高。在人口變動過程中,我國人口與發展的不利關系將逐步呈現🧑🍳,但沒有表現得非常尖銳。長期性的人口萎縮對經濟發展的阻礙關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明。至少到目前的實證數據表明🙅🏻♂️,老齡化和經濟增長是呈現著正向的關系,勞動適齡人口下降和經濟增長也具有正向的關系。對於中國經濟增長而言,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比勞動力的年齡結構仍然更加重要,這使得試圖通過人口政策來解決經濟問題實際上並非是有效的。
在人口政策調整的過渡時期,過分強調“鼓勵生育”🧗🏼,則會凸顯出一些邏輯上的悖論🏄🏼。例如一方面鼓勵生育,一方面還對三孩及以上征收撫養費🫥,這是相互矛盾和政策上相互抵觸的🕵🏻。當前人口政策的逐步轉變,顯然更加需要對生育政策內部的執行、實施方式進行轉向性的調整,並首先放棄對生育數量的行政限製🎽,實現“全面放開♏️、自主生育”,然後才是考慮鼓勵生育的問題🤵🏻。
同時🕧,人口政策也是需要和各種社會政策一起發揮作用的。忽略育齡婦女不願意生育的原因而片面強調“鼓勵生育”,實際上會以損害婦女地位、損害家庭發展為代價,這不僅將事實上和“全面二孩”政策一樣難以奏效👋🏇🏿,而且🍙,在“鼓勵生育”目標下各種對人口生育的調節,例如設立什麽未婚夫婦繳納的生育基金,如果偏離了人口生育的意願,可能也反而帶來負面的反對。
人口政策本身發揮作用的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其他關聯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政策需要有一個相互協調的配套,就業和經濟生產方式的狀況🐤、社會觀念的變化、社會經濟生活的具體環境都需要一個逐步轉變的過程,因此現實的外部環境中🏃♀️,片面倡議“鼓勵生育”是並不必要也並不可行的。
想象中的烏托邦
對很多學者來說,調節性的人口政策還存在一個將人口達到“理想目標”的未來圖景。例如在1980年代初,經過計算將人口目標確定為在2000年達到12億,因此相關聯的就需要極其嚴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實施。在本世紀初,將總和生育率的理想水平確定為1.8,幾乎形成了一個1.8的崇拜👩🏻🦰,這也是基於在2020年達到國民經濟發展目標的理想設計😟🎈。
最近,這種理想狀態也被表現為人口發展的長期均衡。無論是人口的內部均衡𓀎👐🏿,還是外部均衡,可能更加是一種發展的原則💁🏼,而不應是對人口發展的具體衡量。對人口發展的內在均衡,顯然受到了洛特加關於靜止人口的數量模型的影響,以及受到凱菲茲的著名的斷語,即“當一對夫婦生育2個以上的子女,人口就會不斷爆炸👐🏻;而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如果小於2👩❤️👩,人口將會逐步衰亡”🙌🏼。這樣一個考慮下🤚🏻,人口政策如果能夠將人口長期控製在生育二孩的理想狀態,那麽全面二孩政策和按政策生育👧,是有利於人口長期均衡的。
在調節性的人口政策下👮🏻♀️,國家總是有計劃地將人口發展確定出一個目標👼🏿,實際上隱含著一種理想人口狀態的實現💞。這樣的理想的人口狀況🏏,有的時候還與人口容量、人口承載力等概念結合在一起🦉,確定了人口規劃的底線和邊界的限度,成為決定國家或一個地區人口政策的基礎🍤。
實際上正如桑德斯所說,所謂理想的人口、合理的人口無非是一個“概念性的虛數”,是一個指導性的原則。這個理想的人口涉及相當多的指標和各種不同的標準,因此所謂的理想人口的數值👨❤️💋👨🤷🏻♀️,在長期的現實中其實是“存在著但實際找不到”的🚴🏻,或者說,人口實際上是有內在地實現最優的趨勢👴🏽。考慮到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源的不斷開發、技術的進步和資源利用水平的變化,所謂的適度人口和理想的最優值🦯,無非是“想象中的烏托邦”。將人口確定出一個遠期的最優,實際上是不現實的。用這種烏托邦來作為人口政策的指南👨🏿🎨,並直接來幹涉人口的行為,和斧鑿出未來的人口狀況,也實際上往往是削足適履的。
在這個意義上看,主觀地試圖調節人口達到所謂的最優,實際上可能卻往往背離於人口發展的內在規律。人口政策的僵硬調節,固然是以追求最優為目標👨🏼🍳,但是卻可能反而造成了非最優的結果🌬,造成人口與發展的不協調。一些以人口平衡為導向的人口政策🧖🏻♀️,卻往往會造成了新的人口與發展的不平衡。
更主要的是🐣🧑🏿🦲,我們也越來越意識到👫,生育本身是家庭夫婦的自主選擇🚴🏼👩🏽🦱。在生育問題上🌛,國家應該考慮的是為生育提供相應的服務,還不是指導人口生育的行為和數量🧻。政府應該對意願生育的人口提供支持生育的服務,也應該對不意願生育的家庭提供避孕節育的公共服務支持。政府應該加強對於生育的服務🧑🏭,而不是簡單地鼓勵生育🧵🏋🏻♀️。
那麽💜,如果婦女的意願生育率已經是低於政策生育率的,我們需要考慮的不是讓婦女按照政策生育💘,而是需要理解家庭夫婦意願生育率和實際生育行為極低的原因,從而才能改變那些使婦女生育意願不能實現的因素,從而支持婦女生育的理性選擇。不重視采取措施提高家庭夫婦生育的意願和理性,而過分關註在生育行為,那麽強調鼓勵生育🈚️🧑💼,和限製生育一樣🦁🪈,其實都是違反家庭夫婦的利益和需求的。
“鼓勵生育”和“限製生育”都是類似的想法🏊🏼,是過度地幹預了家庭夫婦的生育行為選擇🚝,而忽視了生育本身是家庭夫婦主觀意願和自主選擇的結果。政府的人口政策存在一定的限度,實際上不應越俎代庖地對家庭夫婦的生育行為進行決策🎹,而應通過公共政策改革外部環境,來改變生育者的理性、意願➙,增強他們的知識和選擇性。
因此🎤,調節性人口政策的價值,實際上不在於調節生育的行為🕠💥,而在於調節影響生育意願和生育應為的社會經濟因素👰🏽♀️,影響家庭夫婦對生育的知識、理性和選擇。而這恰恰是當前以生育數量為核心關註的人口政策所未必足夠重視的。
適應性的人口政策
如果說在1970-1990年代💁🏼♀️,人口發展重視調節性的人口政策,具有協調人口發展和經濟增長緊張關系的具體考量🧒🏽🧑🌾,人口政策也在相當程度上具有著促進實現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轉變的主要目的。而在當前時期,人口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緊張關系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人口政策本身對於人口變動的調節作用也在弱化🤦🏽♂️。因此,政府的人口政策應該逐步改變對於生育本身的調節,而應該轉為對於生育的支持和服務,堅持家庭的自主生育和自主選擇,而將人口政策更加轉向於適應家庭夫婦的意願提供生育服務,以及轉向於對人口變動過程的適應🥽。
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在於👩🏽🦲,在日益深化的低生育率社會中🏋️♀️,需要針對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功能的弱化,實施對家庭生活進行支持和加強家庭發展能力的政策。例如對於貧困和低收入家庭的稅收支持,避免他們因為生育增加的經濟負擔而降低生活水平🍺。通過加強對生殖健康服務和嬰幼兒的撫育體系,從而降低因為對子女生育和撫育的壓力造成對家庭的壓力,特別是對婦女的壓力,等等。這些對低生育率社會的家庭支持的福利政策🤾🏽♀️🎹,根據在北歐的實踐👇🏽,也被證明對於提高生育率會發生積極的效果🛌。
低生育率社會下的支持家庭的人口政策也包括增加對老年人口社會照料體系的完善,這實際上是有利於減少家庭夫婦的家庭負擔。這樣一來,看起來是完善了老年社會保障降低了生育子女的需求👷🏼♀️,而在另外的方面🏺,則是完善的老年社會保障實際上是會支持家庭的發展能力⚇,並有利於家庭再生產功能的恢復。
低生育率社會也會進一步增加對國際優質勞動力的遷移需求,有助於幫助緩解勞動力可能會出現的緊張🧝🏻♂️,並發揮遷移對於發展的積極效應🧎🏻♀️。正如同歐洲在第二次人口轉變以後通過遷移來促進人口發展平衡的實現那樣😟,促進移民本身會是低生育率社會內生的人口變動🧔🏽💶。
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強調適應不同人口群體對生育的具體需求👩🏿🦱📒,包括對流動人口👨🏽🎓🙋🏻♂️、低齡的青年、高齡的婦女等,提供有針對性的生育和健康服務。例如,流動人口生育過程的中斷,似乎表現為遷移流動過程對生育影響的常態,但在某種意義上也說明🎀,現在的流動過程本身是非常“不家庭友好”的🙅♂️💆🏻。流動人口過長的工作時間和大量的家庭分離,實際上降低了流動人口生育的可能。這種家庭分離還對家庭夫婦中的男性和女性都產生出健康和家庭生活的風險🧞♂️。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實際上也要求促進流動人口的家庭化遷居,和保障他們具有穩定的家庭生活。
這種適應性的人口政策,本質上不是限製生育、也不是鼓勵生育🏜,而根本上基於家庭夫婦的需求提供生育服務。對於意願生育的婦女提供服務來滿足其“未能實現的懷孕”,同時對不希望生育的家庭也應該對其“未意願的懷孕”提供避孕支持。人口政策應該適應人口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行為👩❤️💋👩🧏🏼♀️,提供相關的技術服務和公共服務🧑💼,這樣才能實現一種全新的基於家庭夫婦生育理性和滿足其具體需求的計劃生育,並扭轉當前計劃生育製度在中國發展面臨的人口政策困境,以及恢復到計劃生育作為家庭計劃的國際潮流的本來含義🧔🏽。
適應性的人口政策也應該強調在生育準備和懷孕期🛼、圍產期、新生兒和嬰幼兒階段,針對人口的具體需求和困難,對與人口再生產相關聯的生殖健康、生育支持🚢♒️、生育服務和撫育等,提供相應的服務。這種對生育服務本身🧚🏼♀️*️⃣,也需要實現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服務🏑,例如對於性和生殖健康的教育實際上是應該從兒童和青少年做起💪🏽,更高育齡年齡的婦女生育服務的必要性正顯得更加迫切,而老年人口的性與健康服務、包括養老服務🙎🏽,也同樣是值得重視和關註的🫸🏼。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總之🧑🏿🎨,在完成人口轉變以後的人口政策,表現出相當的方向性的迷茫,是穩定低生育率、還是“全面二孩”,還是“全面三孩”,還是“鼓勵生育”🔺❣️,似乎陷入政策的陷阱。人口政策在某些地區是鼓勵生育,在有些地區又是限製生育🕯🧑🚀;對某些群體是鼓勵生育,對有些群體又是限製生育;帶來了政策導向和執行的困惑。
為了解決這種矛盾性的局面,人口政策應該弱化其調節性的人口政策的作用,轉型為一種更加強調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實際上😫,改變通過人口政策對人口過程和人口狀況進行調節的想法👴,人口政策就可以不必困擾於對生育是要鼓勵、還是限製;是應該提倡生育二孩🤦🏼,還是三孩,等等實際上並無意義的爭論。
強化人口政策應該適應人口變動和適應人口過程的想法,就可以將生育決策回歸家庭,人口政策則是服務於家庭和適應人口變動。人口政策的基礎是堅持夫婦對於生育的自主選擇,而人口政策是適應低生育率社會的現實、適應不同群體的生育需求🤱、適應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提供生育的服務、教育和指導,而非調節。
適應不同群體的生育需求🏬🧚🏿♂️,從而可以使得生育群體的健康得到保障,撫育得到增強,其包含了生殖健康教育和服務、避孕節育和輔助生殖技術和服務🟫,包括了嬰幼兒的撫育照料、托育托幼和早教發展。適應家庭生育周期不同階段的生育服務👩🏽🦰🪚,則包括增強對生育前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持、對生育過程中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持💫、以及生育以後的公共服務和社會支持🏄🏼♀️。在這些對生育需求的相關領域,則仍然需要重視利用公共部門的力量來支持生育和家庭,幫助人口群體獲得所需要的服務。於是,這種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實際上是架構起對人口生育的宏觀公共服務的公共政策🍚🌸,就是一種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建設。
在這種適應性人口政策視野下的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下🔟👺,就能夠使生育政策轉化為家庭政策;能夠使生育政策對接上福利政策😿。基於家庭的理性選擇🅾️,對家庭生育提供服務和支持🕑,增強家庭的發展能力和家庭福利🐔,這應該成為人口政策的目標。
在這種適應性人口政策視野下的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下,人口政策就可以從對人口進行管理和調控的政策,轉變為對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的政策,提高人民的健康👨🏽🚒、利益和幸福🧑🏿🔧。
在這種適應性人口政策視野下的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下🏃♀️➡️,也能夠支持政府從調控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務政府的轉型👨👩👧👦,並為人口政策奠定合法性的基礎。
同時🧑✈️,也正是由於適應性的人口政策本身增強了家庭發展能力,增加了家庭的生活福利並因此強化了家庭的收入效應🦢,因而🙍🏼♀️,生育友好型社會將能夠內生地促進生育率的提高。這已經從北歐一些國家通過重視家庭的福利製度建設🙆🏽♀️❎,從而帶動了生育率水平的提高的經驗中表現出來。
可見🔯,在人口轉變完成以後,我國人口變動出現了波動性的狀態🧋。人口與發展的緊張關系得到了緩解,而長期很低的生育率狀況迫切要求重新反思中國的人口政策。人口政策需要從促進人口轉變的調節性的人口政策🐫,轉變為在後人口轉變時期,更加適應人口過程和人口動態的適應性的人口政策⚈🧝🏿♀️,從而建設起生育友好的社會機製。這因此也能夠使人口政策得以保障人口的健康和幸福的家庭生活🦞✊,成為滿足人口需求和提高人口生活福利的社會製度,並在宏觀上促進人口和發展的協調🧙🏻♀️。